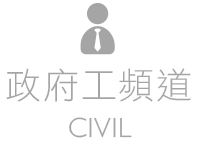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日常看似微不足道的職場互動,可能引發一連串的情緒。而被一個親近的同事傷害時的感受,與被一個陌生同事傷害時的感受有何不同?這種微妙的差異,可能決定了你會選擇原諒、報復,還是離職等反應。
文:人文.島嶼(採訪撰稿:吳景濱|攝影:陳怡瑄)
日常看似微不足道的職場互動,可能引發一連串的情緒——憤怒、恐懼、難過。
臺灣大學管理學院特聘教授戚樹誠致力於研究組織行為和衝突管理等課題。他發現冒犯者與受害者之間的關係類型,竟在這個過程中扮演著關鍵角色。
一個人被一個親近的同事傷害時的感受,與被一個陌生同事傷害時的感受有何不同?這種微妙的差異,可能決定了你會選擇原諒、報復,還是離職等反應。
「家人、熟人、生人」
華人文化重視人際關係結構,可分為家人、熟人和生人三類。家人關係在華人文化中居於最核心的位置,代表著最親密和最值得信賴的圈子。在職場中,這種同心圓的關係可表現為員工的支持和忠誠。
華人文化強調「親疏有別」,人們與內關係的熟人和外關係的生人,相處方式存在顯著差異。熟人可能包括多年的朋友、同學,甚至是經常互動的同事。戚樹誠表示這種差異在職場中尤為明顯。例如,當面對來自「熟人」的不當行為時,人們可能更傾向於原諒或者尋求和解。相反,如果同樣的行為來自「生人」,反應可能就會較嚴厲。這種現象被稱為「內團體偏私」,在華人文化中表現得尤為突出。
對這些人,我們往往會表現出更高的信任度和合作意願。相比之下,對待生人——那些我們不熟悉或剛認識的人,態度可能就會更加謹慎和疏離。
有趣的是,這種關係分類還影響了人們對不同群體的期望和評價。對於被視為「熟人」的同事,人們可能會期待更多的支持和理解。而對「生人」,則可能會保持一定的距離,甚至產生一些刻板印象。
這種差異化的期望可能導致工作分配的不平等和團隊合作的障礙。
內團體偏私與社群集體主義(community collectivism)
華人的關係絕大多數是從「家族」這個單位開始的,傳統上每個人都在為整個家族的福祉著想,個人的成就被視為全家的榮耀,家族的榮耀亦是個人的榮耀。這就是華人集體主義中的自我認同(又稱為自我身份認定)——相依我(interdependent self)文化的生動寫照。
相比之下,個人主義文化的自我認同以「獨立我(independent self)」的概念佔據主導地位。戚樹誠說:「這種概念在歐美較為盛行,一個人從小學到大學的教育系統,都在強調個人能力的培養和自我實現的重要性。這種文化培養了獨立思考、創新精神,但有時也可能導致人與人之間的疏離。」
過去,團體集體主義(group collectivism)這個概念著重在地域性,具相似文化的人形成同一群認同群體,通常聚焦於家庭、宗族或緊密的社交圈。隨著全球化深入各地,社群集體主義概念興起,彌合了傳統家庭集體主義和更開放的社會意識,延伸至更廣的社群。
社群集體主義擴大了「我們」的範圍,強調個人對更大社群的歸屬感和責任感,它鼓勵人們超越家庭或朋友圈,關注和參與更廣泛的社群事務。戚樹誠強調,這種集體主義形式重視社群整體的福祉,而非僅僅關注個人或小群體的利益。這種形式在目前人們經常參與社交媒體(social media)中更常看到,它跳脫過去的地域性,找到彼此相似之處,讓人與人之間產生具「歸屬感」的團體認同。
融入職場的社群集體主義
小J是一家新創公司中負責專案的年輕員工,他剛進入職場不久,對公司內的同事關係還不算太熟悉,但對公司有著很強的使命感,想要透過自己的努力得到大家的認可。
某天,小J在提案會議上向團隊分享了一個經過長期努力構思的創新方案。會後,一位其他部門的資深同事阿K偶然知道了小J的點子,不僅在報告中將小J的點子當作自己的成果發表,甚至在眾人面前批評小J的工作效率不高,意圖削弱他的聲譽。
小J感到深深受挫,憤怒和失望交織在心中,阿K的行為讓他感到不安甚至恐懼,這種情緒讓他無法信任公司內的職場環境。他的心情因為這樣的「不當對待」陷入了生氣與失望的交織中,並產生了離職的念頭。
華人文化中的內團體偏私現象,像是一個同心圓。最內圈是家人和親密朋友,往外依次是同學、同事、同鄉等。對待不同圈子的人,個體會採取不同的互動策略。通常面對內團體的人,我們傾向於理解和和解,而與外團體的人往來,我們往往容易視為威脅。
以上面的故事來說,阿K與小J並無太多交情,在小J的心中,阿K屬於「他們」——生人。這種外關係讓小J感生情緒,進而有逃跑或報復的念頭。
戚樹誠採用故事腳本(scenario)方法進行實驗,戚樹誠團隊的故事腳本描述某人有一個想法或點子被同事剽竊,該同事還在之後的會議上將這個想法作為獨創發表。請受測者當作被偷竊點子者,即被冒犯者,敘述各種情境下的情緒反應。
「我們發現,遭遇職場不當對待時,情緒反應主要是生氣、恐懼和難過,扮演著關鍵的中介角色,連接著不當對待事件與我們的後續行為。當冒犯者為內關係時,被冒犯者會壓抑憤怒,傾向以和解方式處理;如果是外關係的對象,被冒犯者則更容易產生強烈的恐懼感或報復行為。」
恐懼感更像是一個警報系統,提醒我們遠離潛在的危險。當我們在職場中感到威脅時,害怕情緒會觸發被冒犯者的「逃跑」本能,增加離職傾向。相比之下,如果冒犯者是我們相處較為密切的對象(內關係),我們的憤怒可能會相對緩和,報復的衝動也隨之減弱。不當對待雖然同樣令人不快,但可能不會引發如此強烈的恐懼反應。
在職場中,持續的難過情緒可能導致員工採取退縮行為,如曠職或選擇離職,以逃避潛在的傷害。那是正常的,因為當我們感到難過時,我們容易認為自己無力改變現狀,從而降低對改變環境的期待,這種情緒反應在面對外關係冒犯者時更為明顯,同時更感孤立無援。
「我們」
戚樹誠的研究結果顯示,在增強社群(社區)集體主義意識下,可緩和來自外關係者之冒犯行為對恐懼感的影響,進而減弱害怕情緒對離職傾向的影響。此結果呼應了他先前針對團體集體主義意識,可削弱受害者報復動機之類似研究發現。
以上述的故事為例,小J在遭遇阿K的冒犯行為後,感到深深的挫敗與不安。公司內的另一位資深同事阿P察覺到他的情緒低落,並主動關心小J,將小J介紹給其他部門的一些同事,並鼓勵小J參與公司內的跨部門活動。這些活動讓小J逐漸與同事們建立了信任,感受到他不僅僅是自己部門的一員,而是整個組織的一部分。
在強調「關係」的華人文化背景下,戚樹誠表示,組織應建立公正合理的處理機制來應對職場不當對待事件。其次,培養員工的社群(社區)集體主義思維模式可以幫助他們更積極地面對衝突,減少負面情緒和逃避行為。
組織管理者應致力於營造互利互惠的組織環境,增強員工之間的情感聯繫,以減輕人際不當對待造成的負面影響。
戚樹誠提出建立系統化的支持制度,確保員工在遭遇不當對待後能獲得必要的幫助和心理資源,同時對冒犯者實施適當的懲戒或糾正其不當行為、維護職場的合作氛圍等方法都有助於改善。
「其實,過度的同溫層,是造成組織內跨群體衝突的主因。這樣的信念與態度,使其劃分了敵我意識。」戚樹誠熱切地說道:「若能『化敵為友』,將『他們』變成『我們』,群體將更可獲致共容與和諧,能再造不同的可能。」
如故事中的小J遭遇不當對待時,感到孤獨和不安,強烈的情緒反應使他只關注自己的挫敗感和不滿情緒。他對公司和同事的關係是基於個人的感受,當阿P和其他同事伸出援手時,小J開始意識到他並不孤單,其他人對他的支持讓他感受到了一種集體的力量。
他不再僅僅從自己的角度看待問題,而是開始理解同事們的想法和感受。隨著小J認識更多部門夥伴,他逐漸感受到團隊的凝聚力和組織共同的目標。
情感連結促進了他對集體的認同,轉變為一個「我們」的成員,而不僅僅是一個「我」。隨著集體認同的增強,小J的情緒逐漸從憤怒與失望轉向積極應對的心態。
這種集體責任感和對群體利益的關注,正是社群集體主義的核心所在。
Sour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