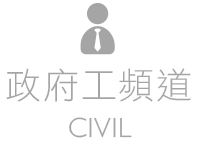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本書會介紹升檔者六大思考模型,作者在戰爭與災難人道援助現場觀察到這些升檔風格,並將其記錄下來。他發現有些同事似乎能將危機帶來的壓力當成養分,讓自己持續成長,有些人則不行。在與愈來愈多形形色色的人共事過後,作者發現升檔風格是可以改變的。透過練習,以及順從自己的天性(你的天性可能符合六大原型其中之一或是更多),每個人都能成為更優秀的升檔者。
文:班.拉馬林詹(Ben Ramalingam)
Chapter 2 激發獨創性
改變思考方式,創造力極速湧現
戰爭為許多人的生活蒙上一層陰影,久久不能散去,但是黑暗之中也有亮光。一九六二年,前二戰美軍傘兵威廉.詹金斯(William Jenkins)來到加州一所醫院求診,他告訴醫生困擾自己近二十年的頭痛症狀愈來愈嚴重了。詹金斯在戰爭期間曾空降至法國境內的敵軍陣營,並與一名德國士兵近身肉搏,期間德國士兵用步槍槍托狠狠地敲了他的腦袋。
戰爭結束後,他到醫院接受治療,試過各種方式但病情仍不見好轉,直到一位年輕的神經手術外科醫生提出一套劍走偏鋒的創新療法。詹金斯同意醫生的提議,並在毫不知情的狀態下成為神經科學界的明星病人,以及諾貝爾獎獲獎研究的主要研究對象,最終成為現代醫學最廣為流傳的神話。
創造力從何而來?創造力位於大腦的哪個區域?我打賭所有人的腦中會立刻浮現「左腦/右腦」的公式,畢竟這套理論自一九八○年代起就廣被世人接受。許多年來,不少人都認為主導思考的大腦半球也會決定一個人的技能、偏好,甚至是性格。這就是神經科學家所謂的「大腦半球模型」,也就是眾人大多認為掌管創造力與情緒的區域位於右腦,理性與邏輯區域位於左腦。
相信不少人都聽別人說過(甚至自己也說過)自己是右腦人或左腦人,最後還會再加上一句:「所以這件事情我做不來。」你明明右腦比較發達,但卻要自己計算公司年報嗎?還是說你明明左腦比較強,但卻必須提出優秀的行銷設計方案?你心裡一定在想:「死定了,我一定會把這兩件事情搞砸。」其實此理論幾乎全都是鬼扯蛋,雖然這些說法已經被踢爆是假的了,而且從來都沒有過科學基礎,但相信的人還是多如牛毛。然而,只要我們拿放大鏡檢視謊言的源頭,便能發現一些重要的事實。
吉爾福特的研究顛覆了整個心理學界,行為科學與彼時正展露頭角的神經科學,而神經科學界那段期間的主要目標,就是要搞清楚發散式與聚斂式思維發生在大腦的哪個區域。在一九六○年代,加州理工學院學者羅傑.斯佩里(Roger Sperry)與麥可.葛詹尼加(Michael Gazzaniga)做了一系列知名的相關實驗。
雖然他們確實發現了一些模式,但他們研究的對象皆為非典型人群。兩人的研究對象全都患有癲癇,而且都接受過一種相當激進的手術療程。透過裂腦手術把大腦分成兩個部分,也就是學界常說的裂腦病患。裂腦手術也就是切除連結大腦半球的胼胝體,看似是種極端且殘忍的手段,事實的確也是如此。此手術於一九四○年代在紐約進行首次臨床試驗,目的是要治療重度癲癇,背後的邏輯是切除胼胝體可以阻斷神經放電,進而預防痙攣在大腦間流竄,摧殘病人的身體。
然而,試驗結果不盡理想,雖然手術確實緩解了一些病患的症狀,但效果卻不夠明確,無法被廣泛用於治療癲癇。於是裂腦手術就被束之高閣,直到一九六二年,威廉.詹金斯的主治醫師才決定使此方法治療他的痙攣。手術結束後,雖然詹金斯的痙攣頻率、強度與時長都大幅降低,但他的思考方式與行為也產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斯佩里和研究生葛詹尼加則是透過觀察與實踐記錄這些改變。
這些實驗中最知名的就是語言與視覺推理實驗,期間研究人員要求詹金斯一看到影像就按下按鈕,接著分別在他的左右眼前快速展示不同的刺激,這些影像資訊則會被傳送相反的大腦半球處理,也就是左眼會將接收到的資訊傳送到右半腦處理。每當研究人員向他的右眼發送刺激(右眼的刺激是針對的是左半腦),他都會按下按鈕,並準確無誤地說出自己看見什麼。但如果研究人員刺激他的左眼(針對右半腦),那他就什麼都看不見。
接著研究人員讓他的左手握住一枝筆,並在他的左眼前快速展示影像,雖然他會說自己什麼都看不見,但卻能用左手畫出影像內容。也就是說,他的左右腦完全不知道另一半體驗到了什麼東西,或是正在做什麼事情。
在一九六○至七○年代間,斯佩里和葛詹尼加等人對詹金斯和其它裂腦病患做了一系列測試與實驗,發現某些認知功能具備「側化」(lateralized)特性,意即某些認知功能只會出現在大腦的特定半球。裂腦病患的左右半腦具備不同的特徵,舉例來說,他們的左半腦具備更強的語言、數字處理與邏輯推理功能,右半腦則側重於視覺與直覺決策功能。
除此之外,他們還得出了一個結論,那就是一九四○年代那群病患的痙攣症狀之所以沒有改善,且術後認知表現也和以前一樣,是因為他們並非徹底的裂腦人。
這項研究結果讓社會大眾和整個創意產業為之瘋狂,一時間各種書籍、課程與訓練法層出不窮,內容都在教人如何掌握大腦「掌管創造力的那一側」。具有藝術、教育和心理學博士身分的藝術家貝蒂.艾德華(Betty Edwards)在一九七九年出版的《像藝術家一樣思考》至今仍是全球銷量最高的藝術類自助書。
根據作者本人的說法,該書的內容靈感是來自詹金斯的繪畫實驗:「弔詭的是,學習繪畫就是學習如何將大腦從左腦模式調整至右腦模式,受過繪畫訓練的人懂得如何調整大腦的模式,而這種轉換思考模式的能力會影響人的整體思維,在用創意解決問題這一方面尤為明顯。」
《像藝術家一樣思考》出版後約十年,美國多棲作家茱莉亞.卡麥隆(Julia Cameron)關於創作的自助書《創作,是心靈療癒的旅程》上市,並用擬人化的筆法,活靈活現地強化了左右腦功能不同的概念:「所有人都被自己內在的完美主義者荼毒,它的名字叫審查員,他就住在我們的左腦裡,不停地從內外批評我們……你可以把審查員想像成漫畫中常見的毒蛇,口中不斷吐出惡毒的話語……邏輯腦就是審查員……藝術腦是發明家,是孩子……創作、全面的大腦……讓邏輯腦學會靠邊站,讓藝術腦大顯身手。」
斯佩里和葛詹尼加的裂腦病患研究內容其實更加細微,而且完全沒有提到健康的人的大腦(相對於裂腦病患的大腦)應該是什麼樣子。他們發現大腦不像一台獨立的電腦,不同的硬體元件有各自專門處理的特定任務。他們認為大腦更像是由數台電腦組成的網路,每台電腦都以纜線連接。大腦不同部分的運作與各活躍腦區間的連接能力其實同等重要,有時甚至更加重要。
裂腦病患研究的真實意義,是要讓大家看見,在不損害大腦特定部位的前提下斷開大部分網路連接會帶來什麼影響。在這種情況下,大腦確實會出現重度側化的現象,導致左右腦分工相當明顯。但是網路功能沒有受損的大腦並不會出現明顯的側化現象,也根本不須要側化,此研究最終為斯佩里贏得一九八一年的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可惜的是,左右腦神經迷思依舊深植在人們心中,荼毒人們的思想。我曾參與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跨政府國際組織,總部設在巴黎)的一項大型大腦與學習專案,擔任創新與創造力顧問,期間赫然發現不少教育專家對大腦的理解居然是錯誤的。這類「神經迷思」不僅缺乏具體的科學證據,更會對教育實踐產生不良影響,其中最為常見的就是左右腦分工理論。
研究人員於二○一二年分別在英國與荷蘭進行調查,發現九成一的英國教師與八成六的荷蘭教師認為個體學習差異源自左右腦思維差異。教師是鼓勵與支持學生學習的重要角色,他們的想法會影響學生的發展、學習、努力程度,以及接觸新科目時的自信程度。
可怕的是不只老師有這種想法,許多專業人士也會將自己歸類為缺乏創造力的人群,在很多情況下甚至認為創造力與視覺藝術有關。這種觀念不僅令人感到遺憾,也與吉爾福特的發散式思維與創造力研究的初衷跟結論背道而馳。
所幸自二○一○年代起,科學思維再次成為主流,在二十世紀中期蔚為風行的吉爾福特思潮終於在二十一世紀再度翻紅。各種相關技術的發展,例如可以測量神經元活動的功能性磁振造影(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使人們能以即時且直接的方式分析大腦在不同背景與情境下的運作方式。
雖然fMRI起初完全是為了醫療用途而生,但這項數位革命確實降低了腦造影工具和技術的成本與提升可攜性,最終被廣泛用於各種背景與情境,例如遭遇突發事件的投資銀行交易員、一級方程式賽車手與外科醫生。多虧這些科技進展,我們才能一窺大腦在處理各種任務時的運作方式。
與此同時,研究人員也小心翼翼,不從腦成象推斷一個人的表現,以免眾人在二十一世紀再次誤信左右腦謬論,並努力讓所有結論都以嚴謹的科學作為基礎。於此同時,學界也開始用像是「連接組預測建模」(connectome-based predictive modeling)這類系統化的方式,追溯大腦網路表現與高層次行為的關連。
連接組預測建模是一種資料密集的研究方式,運作方式如下:研究人員會先獨立分析個體的行為特徵,接著再讓個體接受一系列實驗,要求他們從事各種任務,或是解決不同的問題,並在過程中即時觀測其大腦活動,最後研究人員會在分析報告中尋找與大腦網路活動有關的行為與決策模式。
有愈來愈多研究都想釐清實驗對象在進行獨創或創新思考,尤其是接受吉爾福特的替代用途測驗及其變體測驗時的腦部運作。哈佛大學研究員分析實驗對象在接受替代用途測驗時的大腦活動,發現大腦中有三個系統對獨創式思維相當重要,分別是想像力系統、警覺系統與執行系統。
想像力系統是創造活動(如腦力激盪或做白日夢)的關鍵,此系統除了掌管心理模擬,也負責社會認知,如理解他人感受的能力,或是在特定社會情境中應對進退的能力。想像力系統和探索及參與創新的想法、物件、情境有關。
警覺系統的作用是監測內部和外部刺激,也就是說,警覺系統不僅是我們的內在意識流,也是由我們對周遭事物感知所觸發的外部資訊流。警覺系統會接收無時無刻都在轟炸我們的大量感官資訊,並決定我們該注意及忽視哪些資訊。在決定哪些內部或外部資訊是解決眼前問題的關鍵時,大腦就會啟動警覺系統。此外,警覺系統在神經系統轉換過程中也扮演舉足重的角色,是我們維持專注力與意志力的關鍵要素。
最後是執行系統,此系統負責注意力聚焦、資訊解讀,以及大腦負責決策的各個區域間的溝通。執行系統與一個人使想法變得實際且可行的能力有關,也與準確度、關鍵敏感度、對不同觀點及受眾的意識度有關。
這三種系統在人的思考過程中分別扮演不同的角色,但問題是,接受發散式思維測驗的大腦會是什麼模樣呢?你可能會認為想像力系統是最重要的,但這種想法就和多數人對裂腦研究的解讀一樣,有點過分簡化了。相關證據表明,這三種系統彼此互動的品質與本質才是最重要的。研究人員在檢視接受替代用途測驗的大腦運作後,發現沒有任何一個系統能獨立決定發散式思維。
回想一下自己在思考迴紋針用途時提出的點子,一開始你列出的方法,極有可能都是傳統的用途。幾次過後,你會發現自己提出的用途與來與一般答案不同,而我們也可以從掃描影像看出大腦運作的端倪。測驗開始時,想像力系統的網路會與警覺系統的網路耦合,但耦合狀態並非固定,接著想像力系統的網路會與執行系統的網路耦合,最後想像力系統的網路又會與警覺系統的網路耦合。
也就是說,大腦會不停轉換模式,以動態的方式產生並評估想法這三種系統的網路互動與凱斯.傑瑞在第一章的經歷遙相呼應,也似乎和音樂家創作新作品的狀態不謀而合:
創作新作品時,想像力系統的活動會率先增加,以喚起創造新音樂動機時必要的情緒反應與知覺處理。等腦中形成旋律片段的開頭後,警覺系統就會將你的狀態轉換至執行注意力系統,以便大腦對這段稍縱即逝的旋律產生工作記憶,並專心將其轉換成難忘的樂段。
如果你曾在創作過程中體驗過「火力全開」的感受,那麼現在你應該知道此現象背後的生物學原理了。我們之所以會體驗到這股令人頭昏腦脹的能量與興奮感,完全是因為大腦三大系統的徹底投入。除此之外,這三大系統一共占據了人腦約百分之八十,這項事實打破了另一項神經迷思,那就是人類僅運用了大腦的百分之十。
研究結果顯示,發散式思維得分最高的人不會只固定使用某側大腦,而是會以各種方式活躍地使用整顆大腦。在許多情境中,以及對不少人來說,這三種系統通常是互相對立的。事實證明,很多人會因為出於習慣或懶惰,在決策時更加仰賴特定網路的互動。而隨著時間推移,某些系統就會漸漸成為強烈,甚至是根深蒂固的個人偏好。
在處理發散式思維任務時,大腦中負責這三種系統的區域會產生連網作用。獨創的想法只有在三大系統(具備腦力激盪能力的想像力系統、善於內部—外部監測與學習的警示系統、負責決策且注重細節的執行系統)的連結不停轉換時才會出現。
這三種系統網路的連結與彼此互動的速度,正好是預測一個人發散式思維強弱的最佳因數,這三種系統的網路間連結愈多的人愈有可能跳脫傳統思維框架,想到新的解決方案與可能。除此之外,他們也更有可能具備以系統化方式和順序駕馭不同系統網路聯繫的能力。
發散式思維能力極強的人都具備一種能力,可以同步使用這三種系統網路,且效率遠高於一般人。提出最多獨創性答覆的實驗參與者的大腦網路運作效率也更高,相較於獨創式思維能力較低的人,這些人只須用更少的步驟就能做到跨網路互動。連接組預測建模法顯示,這些神經連結會形成不同決策技巧與風格變體的基礎。此外,我們在本書的第二部分將會發現一個現象,那就是升檔者的技能與這些系統息息相關。
時隔多年,左右腦迷思終於迎來一個理想的結尾,之前提到的哈佛大學發散式思維連網神經科學研究於二○一八年發表於《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當時接受這篇研究的編輯委員正是當年和羅傑.斯佩里一起對威廉.詹金斯進行實驗的麥可.葛詹尼加。人的偏好與習慣並非一成不變,決定這兩項事物的神經網路亦然。吉爾福特堅信創造力是可以隨時間開發的,事實也證明他的想法是正確的,而且在行為層面與神經結構層面也都成立。除此之外,吉爾福特的想法與技術在相關研究中也扮演關鍵的角色。
中國研究人員進行了一項縱向研究,檢視獨創式思維背後的大腦功能與結構如何隨時間變化。研究人員首先使用替代用途測驗遴選並測試參與者,以確保所有參與者在實驗進行之初的發散式思維能力與神經模式都是相似的。測試參與者被分為兩組,其中一組會在接下來的一個月內接受二十次發散式思維訓練,每次訓練時間為三十分鐘,訓練內容除了替代用途測驗,還有其他認知訓練模擬(改善特定的結果,探索不同社會情境的影響),研究人員會在訓練測驗前後分析他們的大腦活動。另一組參與者是對照組,研究人員會在研究結束後分析他們的資料。
僅僅過了一個月,接受簡單發散式思維技巧訓練的測試組,他們的思維熟練度與獨創性都有明顯提升。相較於控制組,測試組提出的想法數量更多,也更具獨創性。除此之外,研究人員也發現測試組參與者的神經結構與功能有顯著的改變。
訓練能提升神經可塑性並不是什麼新鮮事,眾所皆知,接受過訓練的計程車司機,對於空間認知的區域會擴大,但本研究不僅讓學界發看見創造力是可以被傳授的,而且結果也會顯現在大腦灰質上。研究人員可以在分別在我提到的三大系統的神經元活動中觀察到測試組的改變,看見功能的變化,以及互相整合的融洽度。
從第一章的內容得知,一個人看待壓力的方式會引發相應的生理反應,此道理也適用於獨創式思維:思考方式會改變大腦的生理結構。這種情況下的「改變」指的並非只是大腦化學物質的變動,而是一些動搖根本的變革,也就是直接影響神經結構與功能。
此外,研究人員還發現,與者的壓力評估與大腦網路的運行流暢度是有關的。請參考倒U曲線,處於「喚醒」最佳狀態的參與者(即進入挑戰狀態,且並非位於低負荷區或高負荷區的參與者)不僅更有可能讓整個大腦都參與思考過程,提出更多獨創的想法的機率也更高。
然而,為什麼這些研究結果沒有受到廣泛認可,並被用於社會各個領域?為什麼像左右腦分工這樣的神經迷思會被這麼多人接受且如此難以破除,而真正具有科學證據的結論卻僅能在學術圈中流傳?根據我從事人道援助工作的專業經驗判斷,發散式思維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大多數機構都不會獎勵具備發散式思維的人,很多甚至還會主動懲罰具備發散式思維的人。說來諷刺,此現象的罪魁禍首居然就是現代教育系統。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開啟心流的升檔練習:面對壓力與焦慮,運用心態轉換的頓悟,完全解封極限潛能,不靠天賦也能成為頂尖高手。》,方言文化出版
作者:班.拉馬林詹(Ben Ramalingam)
譯者:朱家鴻
momo網路書店
Readmoo讀墨電子書
Pubu電子書城結帳時輸入TNL83,可享全站83折優惠(部分商品除外,如實體、成人及指定優惠商品,不得與其他優惠併用)
透過以上連結購書,《關鍵評論網》將由此獲得分潤收益。
升檔是探索的過程,
讓人們可以化壓力為表現、危機為創意
本書將帶領讀者走遍世界各地,一窺各行各業的人是如何進入升檔狀態,並用這種狀態為自己創造優勢。我們會學到將需求轉換成發明的基本模式,也就是佼佼者處理與控制外部壓力與心理壓力的手法,以及他們用創意回應危機的方式。
升檔狀態適用範圍極廣,不僅家長在管理每週家庭預算時可以用到,員工在排解職場壓力時可以用到,就連在戰場上處理傷員的災害救急人員也可以用到。
回想自己在職場上面臨高效壓力的經歷,你的腦中可能會閃過一個念頭,覺得這種壓力並非威脅,而是挑戰。此時就能開啟通往心流狀態的大門,現在我們有方法能夠主動通過這扇門,這將讓我們得以駕馭這種產生獨創性的力量。
從六大升檔思考模型中,找出符合你的原型
透過練習,成為更優秀的升檔者
本書會介紹升檔者六大思考模型,作者在戰爭與災難人道援助現場觀察到這些升檔風格,並將其記錄下來。他發現有些同事似乎能將危機帶來的壓力當成養分,讓自己持續成長,有些人則不行。
在與愈來愈多形形色色的人共事過後,作者發現升檔風格是可以改變的。透過練習,以及順從自己的天性(你的天性可能符合六大原型其中之一或是更多),每個人都能成為更優秀的升檔者。
第一種是挑戰者:在職場與人際關係中主動嘗試新工作、教學方式的人;
第二種是工藝師:不僅具備創造式思維,還是充滿創意的動手達人;
第三種是結合者:能將不同的領域、專業與知識交會在同一個點,並且能輕鬆跨足各界的人;
第四種是連結者:可以為不同群體搭建構橋樑和網絡、結合眾人社交網絡,以及填平其中的鴻溝來獲得能量的人;
第五種是實證者:動手驗證某個新觀念是否可行的人;
第六種是指揮家:讓具備不同技能且個性迥異的人共事,知曉如何協調眾人想法,促成改革,達成共同的目標的人。
本書特色
- 本書指引出一種高效率的處事之道,從個人生活到職涯發展均有所啟發且適用;
- 當黑天鵝或灰犀牛出現頻率節節升高,需要用更快速且靈活的應對方式來面對挑戰,本書所有的升檔者案例,均是應對危機與逆境的佼佼者,能為讀者開啟嶄新視野;
- 本書的開啟心流升檔三要素,透過練習可穩定觸發大腦「優壓模式」,提升個人生活與工作效能;
- 針對升檔三要素的科學原理、觸發條件與內化方式,作者透過人物故事的詳細解析,讓讀者易於了解原理,能易於掌握內化至個人行為模式的練習要訣;
- 各升檔思考模型均有精彩的原型人物故事,從升檔者的話中,讀者可易於了解各種思考模型的構成模式與運作優勢;
- 每一個升檔思考模型,透過故事介紹都能指出其運作的目標為何,讀者可因應個人需求找出適合自己的模型進行練習方式,增進自身能力解決問題。
Source